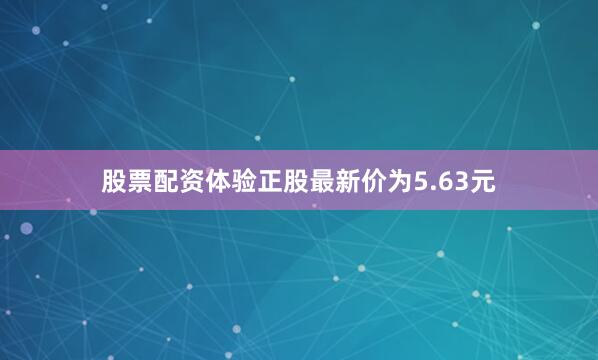郭沫若的酒局
文/张勇
郭沫若的日常生活多姿多彩,他精通书法、酷爱古玩、热衷收藏,这些爱好早已为众人所共知。然而,他一生对酒情有独钟,酒友众多,在无数酒局中,留下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。
“亲吻”胡适
郭沫若生平参与的酒局不计其数,若需从中挑选出最具影响力、屡被后人提及并记录、且蕴含丰富历史意义的酒局,则非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期间,他邀请胡适、徐志摩等文坛巨擘共聚一堂,其中那段与胡适“亲吻”的酒局莫属。
在1923年10月13日的日记里,当事人胡适对那场酒局进行了详尽的记录。
郭沫若盛情邀请共进晚餐,座上嘉宾包括田汉、成仿吾、何公敢、徐志摩以及楼□□,共计七位。郭沫若劝酒之热情,令人难以拒绝。鉴于这是我们和解后的首次重逢,我遂破例举杯,酒量颇大,几近微醺。那一晚,郭沫若、徐志摩和田汉均尽兴而醉。我提及过往欲评析《女神》一事,曾连续五日研读此书,郭沫若听后喜形于色,竟激动地拥抱着我,与我深情一吻。
另一位当事人徐志摩亦于《志摩日记》中有所记载:
日前,沫若在美丽川设宴,恰逢楼适庵自南京抵临,亦受邀与会。席间众人畅饮至醉,楼适庵言辞诚恳,沫若一时情感激动,竟抱住他深情一吻——然而场面瞬间失控,双方拳脚相向,言辞激烈,最终不欢而散,对美丽川之地颇有微词。
1923年10月13日的酒局,胡适与徐志摩的日记记载相互佐证了以下几点:首先,该酒局是由郭沫若倡议举办的;其次,参与者总计七位,均为当时文化界的知名人士;再者,酒局气氛热烈,参与者几乎都饮至醉意;最后,醉酒后他们均表现出较为激动的行为。然而,此次酒局最引人关注的或许并非如此,而是郭沫若为何发起此次宴请,以及他为何对胡适做出了那样夸张的举动。
胡适于1923年5月25日的日记中记载道:踏上征途,拜访了郭沫若、郁达夫、成仿吾诸先生。此行圆满落幕,结束了那场微不足道的文坛纠葛。。”1921年,郭沫若的白话新诗集《女神》问世并广为流传,尽管他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声名鹊起,但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袖相比,郭沫若仍不过是一位初露锋芒的年轻才俊,彼时的文坛焦点无疑是胡适等人。观其新诗集出版之序,1920年胡适的《尝试集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部白话新诗集,无疑开启了先河,而《女神》的问世及其在青年中的风靡,无疑对胡适的权威地位构成了挑战。两位怀抱宏伟抱负、志在千里的知识分子,由此在无形中展开了一场隔空的对决。

胡适
颇具巧思的是,郭沫若与胡适的初次邂逅与相识,同样是在一场酒局之中。他们共同应约出席了商务印书馆高梦旦先生举办的盛大聚会。然而,初次见面时,两人对彼此的印象并不理想。胡适对郭沫若的评价,颇有些微词。他对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。他创作的新诗才华横溢,然而在思想深度上略显模糊,且在艺术功力上尚显不足。”。多年之后,郭沫若仍不忘以讽刺的笔触,如此记载道:
他日日乘坐豪华的大马车,从公馆出发,驶向闸北执行公务。能与这样显赫一时的要人同席,实乃一份莫大的荣幸。
自此,郭沫若与胡适之间的分歧与裂痕愈发加深。然而,胡适并未因此放弃,他屡次向郭沫若伸出友谊之手,主动致信表达和解的愿望。在徐志摩等人的斡旋下,胡适最终登门拜访郭沫若,这标志着双方友谊重建的初步尝试。郭沫若对胡适的诚意心领神会,遂主动邀请胡适及徐志摩等人共聚一堂,畅饮畅谈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,他们自然秉持“和而不同”的君子之交原则。经过一番深入的交流与较量,在酒桌上,胡适对郭沫若有了全新的认识,并肯定了《女神》的创新意义。而热情洋溢的郭沫若亦喜形于色,在胡适脸上深情一吻,流露出了真挚而热烈的情感。
酒逢知己徐悲鸿
1945年2月5日,郭沫若踏上嘉陵江北岸的山巅,步入一座祠堂,携带着周恩来同志所托的延安小米与红枣,探望在此休养的徐悲鸿。他亦借此机会,恳请这位进步人士徐悲鸿及其夫人廖静文,对自己所撰写的战斗檄文《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》给予支持并签署名字。在满腔的爱国热情驱使下,徐悲鸿与廖静文毫不犹豫地在《进言》之书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,以此彰显他们对抗战的坚定支持与鲜明立场。
他们交谈得十分投机,午时已到,廖静文便外出购置了一瓶四川大曲美酒以及佐酒的小菜。鉴于徐悲鸿正卧病在床,廖静文只得亲自陪伴。郭沫若边饮酒,边与徐悲鸿夫妇畅谈,酒逢知己,千杯难尽。在推杯换盏之间,一首《访徐悲鸿醉题》的诗篇便顺势而生。诗中云:
豪情壮志,岂逊千杯烈酒,一骑飞驰,便能闯过万重关山。仿佛有高人击筑高歌,磐溪易水,古今寒意依旧。

徐悲鸿

徐悲鸿《奔马图》赠周总理
本诗以酒为引,广征博引典故,通过描绘太子丹于易水之滨送别荆轲的场景,深情地展现了二人同赴生死、义无反顾的豪迈气概。在更深层次上,诗歌亦寄托了作者对英勇无畏精神的深切赞颂。一骑能冲万仞关是对徐悲鸿《奔马图》的应和。

1956年,周恩来视察徐悲鸿作品展。
郁达夫借酒消愁
在1914年左右,郭沫若与郁达夫相继踏上了日本的留学之旅。彼时,他们正值青春年华,二十岁左右的年纪。面对着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,与积贫积弱的祖国形成鲜明对比,新鲜感、压迫感以及屈辱感交织成复杂的情绪。在这交织之中,“生”的苦闷与“情”的困惑不时在心中涌动。学业的重压与民族的悲运,常常让他们陷入无法释怀的情绪困扰。郭沫若在给郁达夫的信中,如此倾诉道:
即便如今我已来到福冈,那些无名的烦恼依旧如影随形。前几日,我参加了几天的课程,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节奏几乎让我窒息。

1921年,郭沫若(位于左二)、郁达夫(左三)及成仿吾(右一)等文学先驱,于日本东京共同创立了著名的文化团体——创造社。(图片来源于郭沫若纪念馆)

郭沫若日本流亡时作品
在这种心境之下,郭沫若与郁达夫常常相约步入小酒馆,边饮日本清酒,边倾诉对时事、理想与人生的种种不快,借此舒缓内心的烦闷。自创造社成立以来,以郭沫若、郁达夫为首的青年才俊活跃于文坛,成为“五四”时期的耀眼明星。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展开激烈对抗,对胡适的翻译提出质疑,对鲁迅的小说创作进行讽刺,可以说真正激起了“五四”新文坛的波澜壮阔。然而,在这波涛汹涌的文海中,他们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苦涩,即便在外人眼中放荡不羁,内心却也承受着难以言说的压力。于是,“借酒消愁”便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态。
四马路泰东图书局的编译所,就是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仁暂时的栖居之所,胡适、徐志摩等人也亲历过此处,见证了郭沫若落魄的生活环境后,习惯于优雅的徐志摩惊叹道:
然而,凭借四人之手维系一日刊、一月刊、一季刊,其境况必然难以称心如意,生计亦未必宽裕,甚至可能陷入困顿。因此,他们以狂放不羁、叛逆的姿态自居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斯诺、郭沫若、郁达夫三人合影

郭沫若日本全家福
固然,创造社的创立、成长与维系,其间的艰难困苦,恐怕唯有身处其中的郭沫若等同仁方能深刻领悟。四处奔波难免会遭受遍体鳞伤的痛苦,身体的伤痕或许可以愈合,然而他们辛勤编纂、寄予无限期望的《创造》季刊却未能一帆风顺,首期销量不佳,失落之情溢于言表。作为创社的奠基者,同时也是《创造》季刊的编者,郭沫若与郁达夫在听闻这一消息后,无力回天,只能徘徊于四马路的酒肆之中。在推杯换盏间,三十几壶酒迅速入腹,他们自比古代饿死在首阳山的孤竹君之二子。通过这种方式,他们倾诉着内心的悲愤与郁积,抒发着奋发与斗争的豪情。

郭沫若全家合影,归国前。
线上股票配资炒股门户网址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实盘配资网站摩尔线程科创板IPO由中信证券保荐
- 下一篇: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