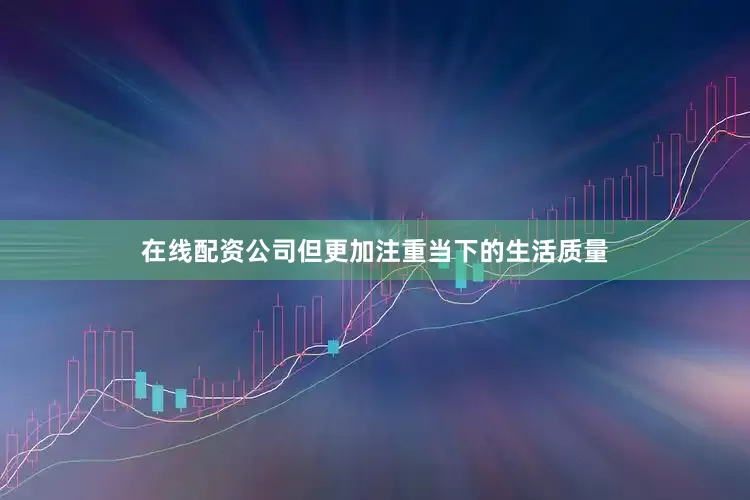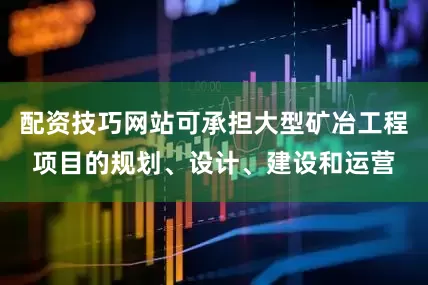在我的老家,有句谚语:“孩子学坏,在根上。”
一个孩子变坏了,不能仅仅批评孩子,还要对孩子的父母,进行教导。
一个坏孩子彻底变好,要么是父母痛改前非的结果,要么是孩子脱离了原生家庭的控制。
可见,从“根上”解决问题,有多么重要。
民国时的红人李叔同,被大家称为“一辈子活成了两世的人”。
他顺利切换人生的轨迹,靠的就是“断根”,是严格自律的体现。
图片
01
李叔同,祖籍在浙江,出生在天津。
父亲李世珍很大年纪,才有李叔同,算是老来得子,因此格外地疼爱,舍得花钱。
在优厚的经济条件下,李叔同也努力读书,却显露出了纨绔子弟的样子。
小时候,他读佛经,和兄弟学僧人的模样,用被套、床罩做袈裟,把炕头当佛堂。闹得很厉害,父亲也不制止。
他也会去青楼,戏剧院等地,和名妓杨翠喜要好,还一起唱唱跳跳。
李叔同和杨翠喜,门不当户不对。一个是官家、富家儿子,一个是卖唱人。因此,他们的爱情,注定得不到祝福。
不过李叔同不死心,离开天津,到上海定居后,还念念不忘,写了很多的信,表达思念。
信中说:“痴魂销一捻,愿化穿花蝶;帘外隔花荫,朝朝香梦沾。”
母亲为了断了李叔同的念想,就“媒妁之言、父母之命”,安排李叔同和俞蓉结婚。
另一边,杨翠喜也嫁给了富商王益孙。李叔同才不得不放手。
作家张爱玲说:“娶了红玫瑰,久而久之,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,白的还是'床前明月光’。”
人这一生,爱情这件事,如果放手了,也不放心;分别了,也不分心,那就会困住自己一辈子。甚至有人,无法取舍,终究导致自己无法顺利踏入婚姻,更无法经营婚姻。
对于功名利禄,李叔同也追求了不少。
他家在上海有钱庄,可以任由支取。他就拿着钱,和许幻园、袁希濂、蔡小香、张小楼四人,打造了“城南草堂”,以写诗文为乐趣。
为了进一步发展,他还去日本留学。期间还认识了一个日本女子,如知己一般。
归国后,他成为了教师。在音乐、美术、戏剧、篆刻等,都很有造诣。
对于兄弟姐妹的关系,他也是耿耿于怀的。
母亲过世的时候,因为身份的妾,按照规矩,出殡不能走正门。这让李叔同很难受,和家人争吵起来。
争执之下,母亲的灵柩也从正门过了,但是哥哥让李叔同带着一笔钱离开。意思很明显,就是分家,各自安好。
感情、地位、利益、名气等,让李叔同一次次受困。
人生多少事,斩草不除根,春风吹又生。
图片
02
一晃就到了三十九岁,李叔同决定出家。
在外人看来,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只有学生丰子恺最懂他:“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,古往今来,十分少有。”
李叔同出家之前,把珍藏的印章,给了丰子恺。
丰子恺很诧异。李叔同淡淡地说:“这些于我,已是负累。”
可见,对于财物,他是彻底断根了。
在李叔同刚刚出家的那一段时间,妻子寻来,一定要说个“为什么”。
他只是委托别人,转告了一句:“当作我患虎疫死,不必再念。”
日本的爱人寻来,他见了最后一面,说:“请叫我弘一。”
也有家书,常常邮寄到寺院里。李叔同一概不打开,只是在信封上写下:“该人已他往,书信原封退回。”
寺院里的人不解,问他为何这样做,起码应该看一下内容吧。
李叔同说:“作为出家人,拆开家书,看到家里有喜事,就会开心;看到不好的事,就会挂怀,还是退了,一了百了......”
很明显,对于人情世故,他是断根了。
做了禅师的李叔同,受邀去青岛讲学。市长沈鸿烈多番请他吃饭,他也拒绝了。
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:“昨日曾将今日期,短榻危坐静思维......”
是的,不在求功名的人,何必和有功名的人同坐呢?一个人吃饭,一个人睡觉,一个人走走看看,挺好的。
最难的,是李叔同对于心态的转变,可谓是断了一切的烦恼之根。
正如《生活的艺术》书里描述的:“咸也好,淡也好,样样都好。能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咀嚼出它的全部滋味,能以欢愉的心情关照出人生的本来面目,这种自在的心性,宛如一轮皓月,大师的内心是何等空灵的境界啊!”
图片
03
断根,对于普通人来说,也是很有意义的。
很多人,吃饭的时候,想着睡觉的时候,做了一个梦。睡觉的时候,想着明天吃什么,回忆晚饭吃了什么。生活中的事情,是彼此交杂的,一样都不愉快。
学会及时切断“刚才的烦恼”,一个人睡觉是睡觉,吃饭是吃饭,幸福感油然而生。
断根,是一种顶级的自律,要做到,也不是特别难。
记住李叔同的一句话:“一音入耳来,万事离心去。”
当下有音乐传来,你马上就忘了过去发生的一切,去享受音乐,时光的频道就切换了。
这个世界,什么都在变,你跟着世界一起变,做什么就是什么,失去什么就不要什么,得到什么就享受什么。
一直活在当下,不透支明天的烦恼,不延续昨天的烦恼。
作者:布衣粗食。
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线上股票配资炒股门户网址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